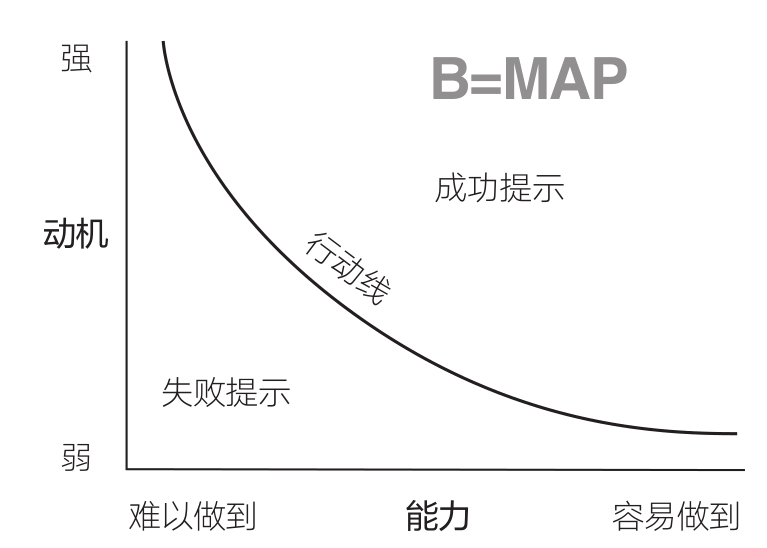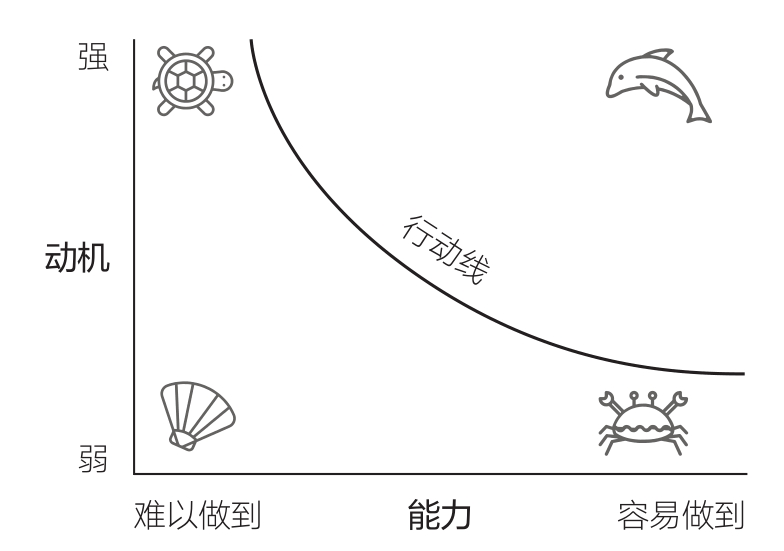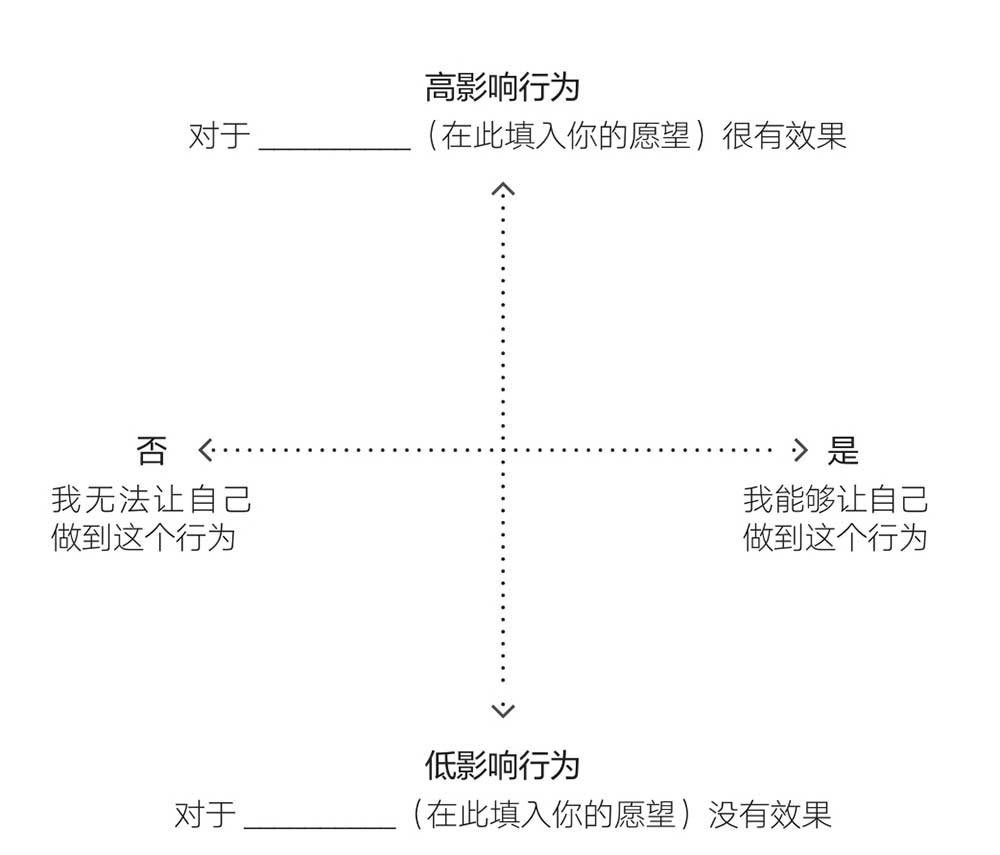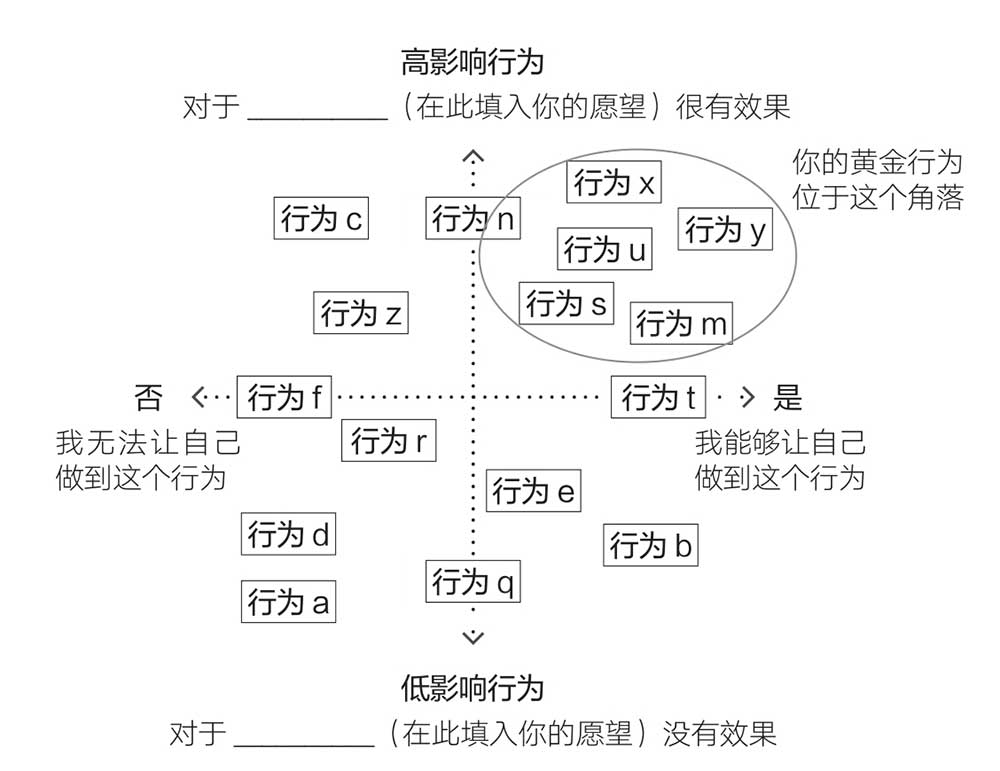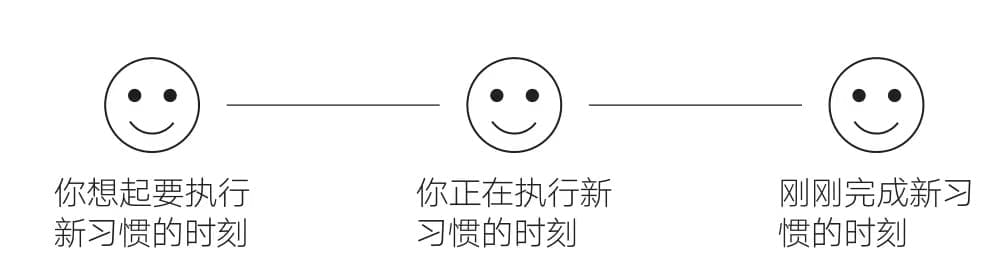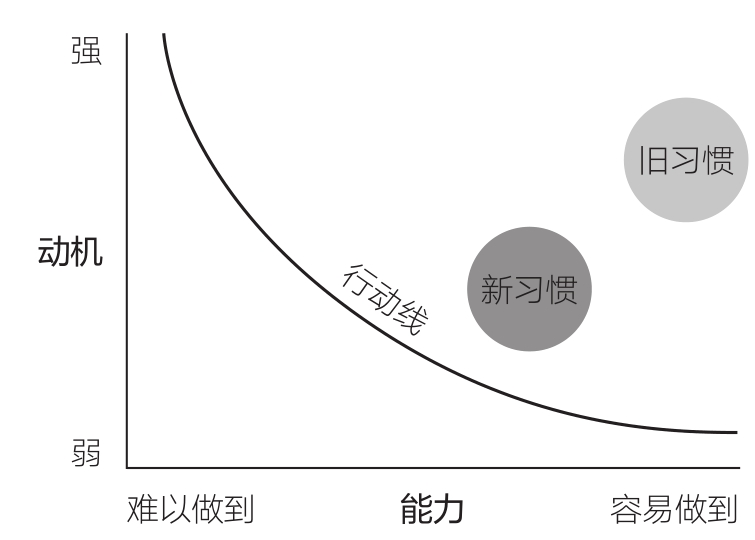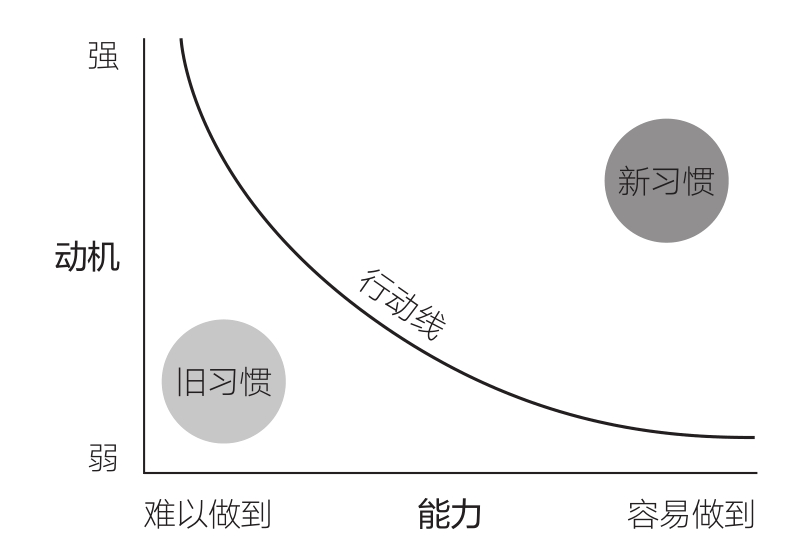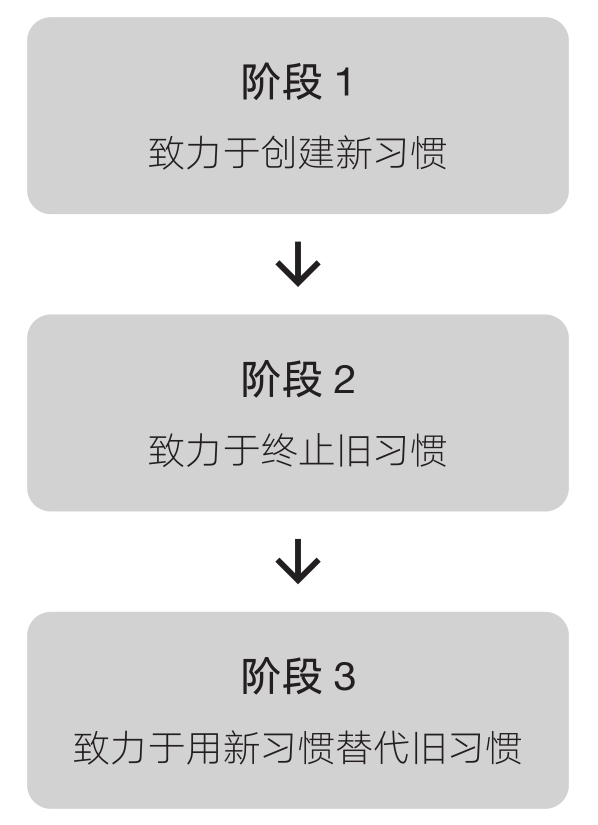📌 只有四种人不会有痒的感觉:出生不久的小孩、老人、刚射完精的男人和刚经历了性高潮的女人。很明显,这四种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性没有要求。弗洛伊德是对的:他认为,痒是“力比多”——即性欲——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据此推断,一个孩子从被胳肢后知道笑开始,便有了性欲。抚摸女人,就会激发她的性欲。当然,这个女人的毛越少,抚摸所产生的效果就会越好。相比于一个浑身长满毛而“不解风情”的女人而言,当然是浑身无毛、一被抚摸就哼哼叽叽地给予男人回应的女人,能够给男人带来更多性乐趣。随着男人的体毛也因为自己母亲的缘故而逐渐脱落之后,他们的身上,也开始有了“痒痒肉”。如今,男人不但喜欢抚摸,同时,也和女人一样,喜欢被抚摸了。于是,人类便有了一种别的动物所不具备的技能——调情
📌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相信,男人之所以喜欢乳房,是因为这两个肉球能让他们重温在母亲怀中吃奶时的童年体验,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还有的人认为,男人之所以喜欢有大乳房的女人,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女人今后会奶水充足,对孩子有利。
📌 那么乳房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没错,它是女人的另一个计谋——对男人的又一次欺骗。在动物界,雄性不会对有着大乳房、正处于哺乳期的雌性有任何兴趣——因为它无法受孕。而女人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要求男人每时每刻都对她保持兴趣,从而有机会获得所需要的帮助。为了迷惑男人,女人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哺乳的时候也和平时一样,没有乳房;要么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有隆起的乳房。前者,是女人无法做到的,现行的措施,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 总的说来,女人的乳房远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重要。它们不过是女人们为了假装自己随时可以怀孕而不得不长出的两大块赘肉。“母性的象征”、“性感的源泉”、德拉克罗瓦笔下自由女神的双乳——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意义的一对乳房,它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和追求……那些一本正经地加诸乳房的“重大意义”,都只不过是些无聊的炒作。一只业绩平淡的股票,要想博取众人持久的关注,庄家就得不断找出题材来加以炒作。女人身体上随便什么部位,要想获得男人额外的关注和兴趣,也需要如此这般地炒作炒作。日本女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露出一截蝤蛴般的后颈,是最能让日本男人动心的部位。三寸金莲,对于中国男人不仅是催情之物,更是文人们创作的动力和题材,国学大师辜鸿铭文章写不下去的时候,赶紧把自己的小脚老婆唤到身边,捧起她的一双金莲放在鼻子底下嗅来嗅去,登时文思泉涌。陶渊明看来也是个超级恋足癖,曾作《闲情赋》一首以明志:“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 不管是什么部位,如果女人们总是用衣物挡着不让男人们看到,男人们就会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屡试不爽的炒作手法!
📌 可是,美国社会学家埃文·罗斯戴尔对1200名妇女做了统计学调查,发现女人真的是胸部越大越聪明呢!她说:“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比如我自己就戴1号胸罩,但是我们的研究证明这的确是事实:胸部丰满的女性与胸部扁平的女性相比,智商高出近10点。”
📌 性高潮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柏拉图在《斐列布斯篇》里描述道:“性高潮让整个身体挛缩起来,浑身乱颤,以致面色陡变,发出各种喘息声,乱喊乱叫,陷入一种极端迷狂之中……”而德谟克里特则言简意赅地总结说:“性交是一种小癫痫。”在希波克拉底看来,性交很像是在调制一杯卡布基诺咖啡——精液产生于脑袋里,经由耳朵流入脊髓和腰部,并储存在那里。交媾的摩擦产生热量,搅动全身上下的体液并形成泡沫。不消说,精液就是那些泡沫成分,像卡布基诺上的奶泡。他甚至认为女人也会产生精液:“在性交中,女人的性器官被摩擦,子宫运动起来,我认为子宫的运动引起了一种心痒,它把快感和热量传遍全身其他部位。”
📌 那么,为什么让一个女人获得性高潮,会如此不容易呢?男人射完精后,从自己性伴的眼中,看到的大多是凄怨和失落的神情。这让男人有了强烈的愧疚感和挫折感——早泄,几乎成了所有男人的一块心病。女权主义的性学家们认为,只要男人在性伴没有达到高潮前就射精,那就算早泄。这个定义,对男人们无疑是过于苛刻了。而医生们从生物学角度出发,认为只要男人有能力将自己的精液射入阴道,从而使配偶怀孕,就不算早泄。面对两种争持不下的意见,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出面作出了一个量化的调和:能够抽送15或更多次之后再射精,就不算早泄。言外之意,抽送15次后,女人能不能体验到快感或是高潮,那就是她们自己的事情了,与男人无关。
📌 如果一个女人,每次都在男人射精前达到高潮,那么,当男人射精的时候,她已经兴致索然了。这样的女人,当然不容易受孕。另一个原因,还是要从“威尔森效应”说起:一个只是偶然才能体验到性高潮快乐的女人,和一个每次都会得到性高潮的女人相比,哪一个会更热衷于房事呢?当然是前者!可见,我们刚巧想反了——正是那些过于容易得到性高潮的女人,才不喜欢性,并且性交后怀孕的几率又小。这种特质的女人,势必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留到今天的,都是令男人们垂头丧气的女人——热衷于性事,却很不容易被满足。
📌 父亲允许长子娶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决定进入“退休”状态,将一家之主的位置让给了长子。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新媳妇一进门,婆婆就得交钥匙——从此以后,家里说了算的就是长子和大儿媳妇了。因此,即便在欧洲为数不多的两代同堂的家庭中,也既没有跋扈的婆婆,更没有受气的儿媳妇。
📌 梅列瓦尔伯爵有一次就忘了预约,当他推开妻子卧室的门之后,发现妻子躺在床上,身边还有一个年轻军官。伯爵不禁温言嗔怪他的妻子:“夫人,您太不小心了,万一进来的是别人呢?”说罢,平静地离开了房间,还带上了门。夫妻二人因为此事而受到整个社交界的高度赞扬:丈夫,是因为他的冷静和有教养;妻子,则是因为她充满“优雅的激情”——在丈夫离开后,她坚持让惊魂未定的情人把刚才被打断的事情做完
📌 这便是游戏规则:丈夫对妻子的不忠要百般容忍、甚至纵容。丈夫的耻辱并不在于戴绿帽子,而是在于吃醋——这完全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将受到整个社交界的耻笑和摒弃;而作为妻子,她的耻辱则在于勾引不到情夫。
📌 在东方,一个男人娶妻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家族的事情。其目的并不是性交,而是“上以承宗嗣、下以事双亲”。至今中国人还是习惯将一个新娘子称为“谁谁家的新媳妇”,而不是某某人的新妻子。而天主教会只是把婚姻看作是为了减少通奸而不得不服下的苦药。所以,在西方人的婚姻中,既没有孩子的地位,更没有父母的地位。如果说中国人的婚姻观是纵向的——其目的只在于敬事父母和生养孩子,那么,西方人的婚姻观则是横向的——其核心只在于夫妻二人。这种观念,无疑也促使了一夫一妻小家庭的产生。在中国,父亲没死就闹着要分家,会被认为是不孝而遭到邻居们的耻笑。而在西方则正相反,结了婚还和父母一起住,那是没能耐养活老婆的窝囊废。所以,在西方几乎见不到三代同堂甚至两代同堂的大家庭,是有其历史和宗教上的原因的。
📌 刘汉初兴,自然要反思前朝的得失。结论是:像秦那样,全是法家的路子,肯定不行,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显然失于“秦法过酷,失天下人心”。可是,走回周朝封建的老路,周朝天子们的窝囊活法当然也是汉朝皇帝们所不愿意的。怎么办呢?只好来个“双轨制”——老六国的地盘分割为9个王国和143个侯国,分别封给各位王子、外戚以及有战功的武将;而秦始皇新开拓的疆域,则直接归中央领导。也是封王的那些王子不争气,一个个都觊觎大宝,起而造反。因此到后来,又全都撤了藩。晋得天下之后,晋武帝也得琢磨琢磨曹魏错在什么地方。得出的结论:曹魏宗室太弱,曹奂被司马炎欺负的时候,没有哥儿们弟兄来救他。于是,晋大封宗室,还硬性规定每个封侯国内应该有多少兵马。日后,引发“八王之乱”,司马弟兄们一通乱打,终使西晋灭亡。从此,中国再也没人敢提“封建”二字。以后的历朝各代,全是清一色的中央集权
📌 可是在欧洲,最大的贵族领地内也不过几千户人家。每多产生出一个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就意味着能多收一份赋税。所以贵族愿意并且能够对领地做出精确的数字化管理。可古代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一个地方官员管理的地域,经常比欧洲整个一个王国还要大。可他却只是皇帝手下的一个打工仔,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他的官职所规定的俸禄,而与所辖区域的实际税收无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朝官员最喜欢做的都是两件同样的事情:对上谎报灾情,要求得到减税减赋的优惠政策;对下建立两本账,将新增人口和开拓荒地产生出的这部分税收揣进自己的腰包。所以中国的文官和欧洲的贵族正相反:他们既不能更不愿意进行精确的数字化管理。
📌 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中央集权统治者的青睐,无非是因为“君臣父子”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宣扬忠君思想;后两个字,确立了父亲的地位,从而鼓励了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的建立。大家庭甚至宗族的建立,大大简化了统治者管理的难度。对于低效而夹杂着私心的文官系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于是,秦以后各朝甚至不惜动用法律的手段来确立一个大家庭中父亲的绝对权威:子女必须“为父母讳、为父母隐”,如果一个儿子去向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犯了罪,被告的父亲到底有没有罪尚需进一步核实,而这个原告的儿子,“忤逆”之罪却是确凿无疑的。他告他父亲什么罪名,就将以什么罪名对他本人进行处罚。在这种法律条文之下,父亲的权威可想而知。一种思想在一个社会中长期霸占着独尊的地位,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僵化和停滞。中国的儒学和欧洲的天主教一样,成为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制约因素,便不足为怪了。汉及魏晋之时,一个人要想做官,必须由乡里长老向朝廷推荐,称为“举孝廉”。从名字上即可看出,一个人要想得到这种推荐,他就必须在孝道和人品方面有突出表现才行。按儒家的思想,如果一个人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好,又怎么能“治国平天下”呢?汉初之时,陈平虽然有“盗嫂”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却仍然可以凭借在几家人之间把一块猪肉分得比较公平而被推举做了官。到了讲究门阀的晋朝,寒士们得以擢升的机会大大减少,光会分猪肉可就不行了。要想当官,就必须在“孝”字上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壮举才行。这就使得孝顺父母这一正常举动变得越来越夸张、越来越成做秀。王祥卧冰、郭巨埋儿之后,中国做儿女的算是倒了大霉:如果父母生了病,儿女要从自己大腿上片一块肉下来做药引子不说,还得尝尝父母的大便是什么味道,才能算是孝。据说,如果病有治,大便就是咸的;如果病没治了,大便就会发甜。本来,儒家的孝道并没有这么过分。孔子对于孝的要求,仅止于“养颜”,就是得让父母开心。子女对于父母的态度,只是“无违”,只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本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自从汉以“孝廉举士”之后,孝道变成了一个人升官发财的途径,这才使得对父母的孝顺变得过分和做作起来。这大大强化了大家庭中父母的地位。在一个家庭中,儿子都没什么地位,又何论他的妻子呢?
📌 在一个宗族中,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几个大家长的共同祖先——当然,他早就死了,变成了宗祠里的一个牌位。为了统一思想,便需要假托祖宗的名义建立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家法,这便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此,家长的权威便制度化了。在一个宗族中,所有财物都要上交宗族长,再由他分配到各个小家庭中去,每一个小家庭都不能有私房钱。
📌 理学之真正得势,是在宋元之后的明朝。花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偏偏对朱熹的学说偏爱有加。这种偏爱与其说是熟读诸子百家后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出自两个人都姓朱的巧合。朱元璋规定科举的考试范围只限于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是理学大盛的原因。自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妇孺皆知了。可事实上,对中国人为害甚大、甚久的理学之所以得势,却是源自朱元璋的一个怪念头:他不喜欢现金。
📌 除了机遇之外,另一个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经济。如果妻子能够经济独立,她通奸的胆子自然就要大得多。妇女的财产,表现在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以及对丈夫遗产的继承权上。对于一个已婚妇女来说,通奸最大的风险就是婚姻破裂。而欧洲妻子和中国妻子离婚的难度是不同的。前者因为天主教禁止离婚的缘故,离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通奸带来的离婚风险很小;而后者的婚姻并没有什么保障。即使丈夫很爱她,但只要婆婆不喜欢,她也多半会被赶回娘家。在中国,关于休妻有“七出三不去”的法律规定,“七出”分别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和恶疾;“三不去”的具体内容是: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以及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曾经得过人家嫁妆而现在妻子娘家已经没有人可以投靠的、已经替公婆守过三年孝的、娶妻的时候很穷而升官发财之后想起闹离婚的,这三种情况都不得休妻——这大概就是中国妇女婚姻仅有的保护措施了。并且,“淫佚”之罪是不在“三不去”的保护之内的。
📌 日耳曼人认为妻子从娘家继承来的财产属于她的个人财产,丈夫无权处分;二是教会法——为了避免丈夫死后妻子陷入生活困难,天主教会规定,男女结合前必须划出一笔抚养寡妇的财产,这笔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克减,否则,任何婚姻契约均不得缔结。通过这个规定不难看出,在中国,丈夫将聘礼付给了妻子的父亲;而在欧洲,则是付给了妻子本人。除了对嫁妆的支配权外,欧洲妻子还有继承权。她不仅是丈夫遗产的第一继承人,而且即便出嫁以后,她也有权力继承她父母的遗产,只是比她的兄弟分到的要少些。不过,有一条对她特别有利的规定就是:母亲的嫁妆只能由女儿来继承,其他人无权染指
📌 中国的父母对女儿是慷慨的,大多数时候,嫁女儿付出的嫁妆比娶儿媳妇付出的聘礼要多出不少。汉文帝就曾苦恼于民间风俗对嫁妆要求过高而导致大量溺杀女婴,因而多次下诏要求婚事从俭。关于宋代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范仲淹立的家法中管窥一斑:范家嫁女支钱37贯还多,改嫁支钱20贯;娶妇则支钱20贯,再娶不支。
📌 整个唐朝是胡化十分严重的时期。从唐高宗李治立父亲唐太宗的妃子武则天为后、到唐明皇李隆基立儿子李瑁的妻子杨玉环为贵妃,便可看出其早期父系氏族社会父子共妻的风俗遗迹。而我们知道,在这种父权制的早期形态中,必然又会残存母系社会的一些观念——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性自由的遗风也颇为严重。所以唐朝才会有武则天当女皇并大蓄男妾、皇宫内嫔妃屡有秽行,以及太平公主的淫荡和权倾一时。
📌 一个中国女人不论生在多么富的家庭、或是嫁到多么富的家庭,她这一辈子都与财产无缘——父母凭一份嫁妆剥夺了她出嫁后继承娘家遗产的权利;而嫁到婆家后,她又失去了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她的任务,仅限于生下能够继承财产的男性后代。如果她没有儿子就守了寡,夫家宗族会过继一个男孩给她,让这个与她无关的孩子继承她亡夫的财产以及她自己的嫁妆;如果要改嫁,那除了羞辱,她什么也别想带走。而在帝国政府眼里,女人根本就不能算人。国家既不给她权力,也不让她承担义务。而在法律方面,不论丈夫做了什么,妻子都不允许起诉他。
📌 恩格斯将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描述为“以通奸和卖淫作为必要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这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区别只在于下层男士更多地选择嫖娼,因为它干脆利落且花费不多;而衣食无虞的上层男士却更喜欢通奸,因为它带来了冒险的刺激。戴绿帽子的丈夫和红杏出墙的妻子——这是一夫一妻这场冗长而沉闷的大戏中,间或跑出来调节气氛的小丑,深受全体观众们的喜爱。
📌 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的财产继承是在所有儿子间分配——嫡出、庶出,甚至私生子都有份。而在欧洲,土地只由长子继承,次子们离家另谋生路。
📌 毫无出路的悲惨境地必然引发道德上病态的狂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中国妇女被一副枷锁束缚得一点儿也动不了的时候,她就会将这副枷锁拉得更紧——毕竟,这是她能做的唯一还称得上主动的事情
📌 19世纪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为例——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像地狱的地方:狭小的厂房内塞入尽可能多的男女工人,彼此间除了传染死亡率高达72%的结核病之外,还毫无羞耻地滥交。缝纫女工每周工作7天,每天18个小时。下班回到不足15平方米的家中之后,立即倒在大床上,像石头掉进水里一样沉睡过去。大床上,还挤着父母和兄弟。屋角放着一张单人床,那是出租给单身的房客赚几个便士贴补家用的。有一位不到20岁的缝纫女工,在“未曾感觉到与人性交过”的情况下怀了孕。一位议员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她的父亲、兄弟,还是那个房客?睡眼惺忪的女工回答道:“这有什么区别吗,先生?
📌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性生活、爱情和婚姻应该“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那你就应该娶她,然后,一辈子只和她一个人做爱。在人类430万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制的时间只有6000年。而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这个念头,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0年!看来,令人惊愕的倒不是这个荒谬的念头何以会产生,而是它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
📌 再来看看婚姻:这东西只存在了6000年。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了剩余财富,以及男人们想把这些财富传给自己亲骨肉的小心眼儿。可见现行的婚姻制度,其核心是孩子和财产。不是性,更不是什么爱情。
📌 美国的一个研究表明:不论一个男人起先多么喜欢一个女人,和她连续做爱15次之后,他的“性”趣就会开始减弱。前些年出现了一个词儿,叫“丁克”(double incomes no kid),意思是两口子都工作但不要孩子——这真是有史以来最荒诞的男女关系。不要孩子,又有什么理由结婚呢?一夫一妻这个婚姻制度,出发点就是孩子嘛!相比之下,倒是近年来由“丁克”派生出的一个新词儿“丁斯”(double incomes no sex)——意思是两口子都工作但不同房——显得更“正常”些。
📌 套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看来美满婚姻是这样形成的:夫妻二人恰好都有一点儿自恋,还都有程度和类型正好相同的神经官能症,他们彼此通过移情,把情结恰巧都投射到对方身上,并形成“固化”。于是,他们两人终生美满、和谐和幸福了——整个过程,看上去像自由体操结束时那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筋斗。如此高难度的事情,凡夫俗子们也只有当观众的份儿了——体操在中央五台,美满婚姻在中央八台。
📌 。一位接受调查的北京离婚女性对婚内和婚外的性做了比较:“我们(指她与前夫)在离婚后还偶尔有性关系——作为情人。他离婚后和一个女孩儿同居,每次都是偷偷摸摸到我这儿来。在婚内,每10次性生活我大约只有1次快感;在婚外,10次里9次有快感……”瞧,同一个男人!
📌 在漫长的狩猎采集时期,一个女人的策略恰好是把水搅浑,让尽可能多的男人认为他可能是她的孩子的父亲——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多父”理论。也就是说,恰恰是女人,为了孩子的利益,才更热衷于滥交。让很多男人对自己的孩子“有好感”,远好过要某一个男人百分百负全责。因为,男人的责任感终究不是那么靠得住。另一个女人——只要她稍微白净一点儿、胸围大一号、再年轻个三四岁,就足以让男人的责任感荡然无存。所以,采取“多父”策略的雌性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灵长类,以及存在至今的人类母系社会。女人的贞洁,完全是源于后天的文化建构,而与生物本能相违。前文提到的巴拉圭北部的埃克印第安人,每个孩子通常至少会有三个父亲:第一个是他出生时与他母亲有婚姻关系的男人;第二个是他母亲怀孕前后与她睡过觉的男人——这种父亲通常不止一个;第三个父亲,则是他母亲自己确信使她受孕的男人。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这三个父亲并没有什么差别——都相当不错。
📌 为了证明“男人比女人更爱滥交”的结论,进化心理学家们还做了个试验:找几个靓女帅哥,跑到大学校园里去分别勾引男女大学生。结果:愿意发生性关系的男生是75%;而愿意发生性关系的女生则是0。于是进化心理学家们得出结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滥交。可是,这样的试验结果靠得住吗?在一个同时有10个女朋友被誉为风流倜傥、而同时有两个男朋友就会被斥为“母狗”的社会里,在一个男人普遍富于攻击性、女人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这样的试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 6000年的时间里,男人给了女人两样东西:一副枷锁和对丧失这副枷锁的恐惧。当枷锁被打开之后,恐惧却阴魂不散。女人在恐惧中嗫嚅着:“我要一个丈夫,我要结婚。”就这样,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已婚妇女,通过从属于某个男人,得到了这个男权社会的认可和接纳。对于进化心理学家们得出的关于“女人天生贞洁、天性喜爱家庭生活”的信誓旦旦的所谓结论,西蒙娜·德·波伏娃早有预见地事先就做好了回答:“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被造就的!”
📌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大声宣扬女同性恋——即使不喜欢也至少应该尝试一下,以便把“和男人睡在一起”从唯一的选择转变为众多选择之一。
📌 以当时的观点来看,性交不过是两个人全身皮肤外加一小段粘膜彼此摩擦一小会儿罢了,除了一身臭汗和疲乏感之外,不应该再产生任何其他效果。
📌 存在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生是痛苦的”和“世界是荒谬的”——直接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萨特将“存在先于本质”定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命题,意思即“事物的本质是由人赋予的”。从这个命题不难看出:存在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要让人去僭越神的位置。从此,上帝从高高在上的天国跌落至每个人的内心——由先前的above everyone变成了within everyone。这使得每个人早上起床洗漱的时候,从镜子中直接看到了神——他本人!于是,人人都跟着萨特喊他那句著名的口号:“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既然“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可“人生却是痛苦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阻止自己及时行乐呢?另外,“世界又是荒谬的”,那么,还有什么清规戒律是值得尊重的呢?
📌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情况: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这一情况给社会各层面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今天,消费居然成了需要商家发掘、刺激和引导的事情。人不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被劳动所异化”,而是——被弗洛姆精准地指出——被消费所异化。
📌 理性的消费已经不能填饱机器的胃口,商家需要消费者“无理性”地消费。方法自然是创造时尚和品牌。人们愿意多花5000块钱购买一款新手机,只是因为显示屏是蓝色的——第二年这款手机就降到了500块。可这并不妨碍消费者继续购买今年的新款——又多花5000块钱——这次为的是手机可以拍照,尽管他们心里明白,花5000块钱可以买一个非常好的照相机,比手机拍照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 在这种情况下,性交自然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和经历,甚至干脆就是一种消费行为!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需要的只是一小会儿前后摆动的运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性解放浪潮中,人们拒绝和同一性伴做爱超过一次——同一种经历,没必要再来一次。在谈到消费的时候,弗洛姆这样说道:“五花八门的消费给人造成最大的幻觉是,消费者自以为是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享受,实际上却浑然不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只需将这句话中的“消费”改成“性交”,“财产”改成“身体”,便可将其作为性解放运动最好的总结。
📌 这种后现代观念还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一个老姑娘会比一个离婚女人承受的压力更大: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一个老姑娘更像是个无人问津的商品——这是消费社会中最大的失败;而相比之下,一个离婚女人不过是一个被用旧的商品罢了——至少,她被消费过。
📌 一个妻子与人通奸自然要受到最重的惩罚。因为,她动摇了父权制社会得以建立的最根本目的——男人获得合法继承人。因此,一个通奸的犹太妻子是要被乱石砸死的;而惩罚一个男人的通奸行为,则是因为他损害了另一个男人的财产:如果他是与一个已婚妇女通奸,他会被罚得重些——通常,是和“淫妇”一起被乱石砸死——因为他危及了那个丈夫的所有财产;如果他与一个未婚姑娘通奸,则会被罚得轻些——因为,他损害的只是那个做父亲的一部分财产。《旧约》中规定:如果一个男人与一个处女性交而被人看见——这个姑娘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被损害了——他必须向姑娘的父亲赔一笔钱。然后,不管他爱不爱这个姑娘,也不管他是不是已经有了老婆,他都得把这个姑娘娶回家。
📌 以法国为例。首先,从“人人平等”的前提出发,法国认为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因为其与异性交往的模式“与众不同”而受到损害。因此,政府承认独身者、未婚妈妈、异性同居者和同性恋同居者一切人等,与已婚者享有相同的权利。这样,虽然它并没有直接否认婚姻,却承认不结婚的和结婚的完全一样。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婚姻。就这样,法国政府把关注点完全转到了孩子身上,至于成年人之间以何种方式相处——结婚还是不结婚,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同居还是单身——政府干脆无所谓。
📌 有了钱之后,法国政府便给每个孩子——不论生在穷的还是富的家庭,也不管是婚生、非婚生还是领养来的——发同样数额的津贴。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得到的子女津贴数相当于法国男性平均工资的9.5%。津贴一直发到孩子满18岁——相比之下,日本才给每个孩子发50美元,而且只发到6岁。考虑到相比于双亲家庭,单亲家庭在抚养孩子中所处的弱势,法国政府除了按孩子人头发放的“大锅饭”之外,还专门给单亲家庭发放额外的补助,以避免他们陷入贫困。光给孩子发钱是不够的。要想做一个好“父亲”,还必须照顾好孩子的母亲。在这方面,法国政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A)早在1913年,法国就通过了妇女“带薪休产假”的法案。今天,法国妇女在生头两胎的时候,都能享受到“强制性”的16周带薪产假。期间可拿到80%的净工资,产假结束后可继续回去工作。如果生更多的孩子或是双胞胎,产假更长。B)产假结束后,在孩子满3岁前,或家中有两个孩子要照料时,父母双方可任选其一留在家中照看孩子。在此期间,国家仍然发给工资。孩子满3岁之后,由政府负责为留在家里的那个家长重新安排和他以前从事的差不多的工作。C)高质量的、全日制的和廉价的托幼中心,以解除“工作妈妈”们的后顾之忧。法国公共托幼中心的质量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大多数不工作的家庭主妇也会把孩子送到托幼中心去,以便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另外,收费也十分低廉,通常不超过一个普通家庭收入的10%~15%;而低收入家庭,则享受免费待遇。如果双职工父母不把孩子送到托儿中心,而是雇人到家里来照料孩子,国家同样发给补助。以上的种种措施,得出的结果自然是令人满意的。在法国,每年投在儿童福利上的资金,占其GDP的10.7%。相应的,儿童贫困率则为2.6%(见图7)。这个数字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法国人均收入比日本还要低。国家作为“公共父亲”的表现是如此出色,法国的男人们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以父亲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遭受更大的冲击——和美国相比,法国的离婚率虽然差不多,可结婚率却只有美国的一半。2002年美国的一个人口调查在比较了结婚、同居和单身的增长趋势之后,不无忧虑地说道:“10年内,结婚将成为少数美国人的选择。”而这种情况,在法国则早已成为现实。
📌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法国和美国的妇女就业率是最高的(46% vs 47%)。所不同的是,美国妇女更多的只是“部分时间用于工作”的不充分就业,而法国妇女更多的则是“全日制”的充分就业。另外,得益于良好的托幼系统,在25~39岁这个年龄段,有78.8%的法国妇女参加工作——远高于美国,更高于日本。
📌 法国政府认为,一个孩子没有父亲,恰好是政府多给这一对母子救济的理由。在美国50个州中,只有威斯康星州对无法确定父亲身份的孩子没有歧视。美国人做了个调查:穷爸爸如果不需要赖账,他和孩子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否则,他往往就不见了踪影。令人感到不解的倒不是这个调查的结果,而是美国人何以要做这个结论不言自明的调查;E)在苛刻非婚生子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向一对已婚者征收比两个单身加起来更多的税。理由似乎是:两个人合伙养孩子,相比于单亲家庭是占了便宜——美国政府也实在是太会算计了;F)直到1993年,美国妇女才有休产假一说,而且仅限于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里工作的雇员——为期12周,没有薪水;因此不难理解,在符合条件的妇女当中,有64%放弃了产假——因为她们“休不起”;
📌 在一个国家中,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越厉害,这个国家就越是“男性化”、越是富于侵略性。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各地到处惹是生非的会是美国和英国,而不是法国或瑞典。至于日本,因为受制于“战后宪法”,它失去了向海外派兵的权力。即便如此,它还是通过出钱给美国,从中得到了“参战”的快感——一种类似于买鞭炮请别人放的“快感”。尽管那鞭炮的响声,往往要在“意淫”中才听得真切。
法国政府承认独身者、未婚妈妈、异性同居者和同性恋同居者一切人等,与已婚者享有相同的权利。这样,虽然它并没有直接否认婚姻,却承认不结婚的和结婚的完全一样。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婚姻。 ^225207353-7JnDxdNkA
⏱ 2023-07-01 15:20:22